

耄耋之年上崇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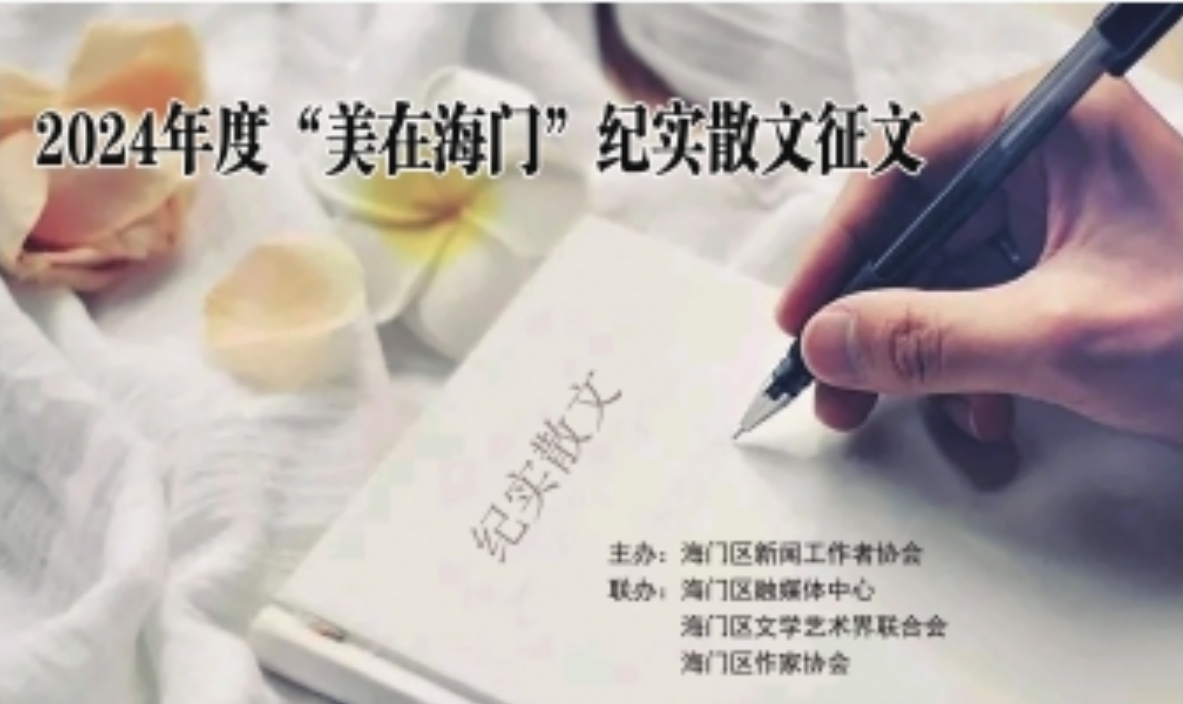
□王剑飞
父亲曾在永隆沙筑堤围垦5个多月,一直想去当年的芦苇荡看看。老母亲80出头,因身体原因且晕车怕乘车,多年不敢出远门。经父亲三番五次地劝说后,母亲终于答应跟我们一块上崇明岛。
在阳光明媚的春光里,我早上7点钟就从海门城区开车出发来到了乡下,不到8点就往崇明岛进发。前一天母亲还特意去天补镇染了头发。临出发上车前,父母亲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。母亲说他要坐副驾驶位,前排视野开阔,晕车时感觉好受些。
从农村小路上了336绕城线,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时,母亲从包里取出一只红色塑料袋,右手紧抓着。母亲觉察到了我好奇的眼神,就解释着,路上晕车要反胃,塑料袋时时刻刻备着,就不会弄脏我的车。于是我车开得很慢,也从不急刹车。一个多小时后,汽车向南穿过两侧都是香樟和水杉树的玲珑湖路后,江声滔滔,空气清新,令人心旷神怡。
在天然氧吧式的临永汽渡口,我与父母上了摆渡船,浪花和汽笛声伴着我们向花香海永靠拢。此时,母亲讲起在我童年时,她用自行车带我来青龙港看江看轮船的往事,我从那时起就立志当海军,最后我成了崇明岛号万吨大舰的指挥员。微微江风中,我搀扶着母亲下车到渡船舷边,向北眺望壮丽的长江和美丽的海门,我无意中发现她手中还是拿着那个红色塑料袋,或许是母亲怕晕船,仍然备着袋子。
过了临永汽渡,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海永镇。崇明岛上这块海门热土,如今“近看是花海,远看是森林”,昔日荒芜的芦苇荡变成了肥沃的良田,海永成了生态景观示范区和休闲度假体验区。87岁的老父亲非要让我带他到防岸堤上看看。上世纪70年代他在永隆沙筑坝和修建防岸堤近半年,主要对永隆沙的南沿、北沿、西端以及海永沙实施二期围垦。父亲说当时涨起来的永隆沙都是芦苇荡,白天挖泥做岸,晚上睡在茅草房,吃的是本地自产的洋扁豆、土豆、白菜和烧饼,偶然能在江边抓到螃蜞和鲥鱼,那是难得的加餐了。
岁月在岸防堤上剥落,留在父亲记忆里的美好被时间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父亲在江沙背上种植芦苇、在江堤上垒石头的情景。眼前,长江水拂过江堤,一块块被时光磨平了的大石头,仍然整整齐齐守护着海永镇的北岸。带着花草的香气,我们穿过那混合着泥土气息的江堤树林,一群麻雀从湛蓝的天空飞来,落在充满生机和富庶田野上,顿感脚下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海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。岁月静好,时光易老,长沟流月去无声,父亲对这块江中热土的挚爱永存。
第二站来到了崇明城区的南门医院,三娘姨今年84岁,60多年前远嫁崇明,身体一直欠佳,近20年没下过崇明岛。老姐妹俩多年不见,在病房里再相逢,相互抚摸着脸,手拉着手不肯放下。
隔壁床位的病友跟我说:“你娘姨身体虚弱,这几天一直精神恍惚,听说娘家人要来,今天一大早精神头就很足。”病房中,姐妹俩有着滔滔不绝的话语,边叙旧边互相鼓励,共度时艰。隔江而来的姐妹情,使三娘姨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种割不断的亲情,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!周围的亲戚和同房的病友都热泪盈眶,不知不觉,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
第三站是老仇家。当年围垦场里没有电视,交通又不便。太阳落山后,茅草房里,大家你看看我,我瞧瞧你,非常寂寞。父亲是个文艺青年,曾经在海门文化馆工作过,阅读了不少书,他就主动站出来,义务给大家讲故事。后来,每到夜幕降临,当地四邻八沙的农民都搬来小板凳,大家坐得整整齐齐来听故事。老仇当年是小仇,听故事他是最积极的一个,至今他还记得父亲在芦苇荡茅草饭堂里讲的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和《青春之歌》等精彩片段。老仇说:“当时围垦和筑岸一天劳作后全身是汗迹,到了晚上不但累,而且洗澡成了难题,但只要听到父亲那生动的故事,浑身又充满了干劲。”
老仇是海门悦来人,因支援围垦认识崇明姑娘翠珍后,在庙镇结婚成家,现在居住在庙镇西侧的米洪村。父亲几十年后,重返故地,见到了那个年代听他讲故事的人,激动万分。汽渡每天傍晚6点半下班停运,两对老夫妻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,不知不觉,太阳快西下。老仇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,说要么在他家住一晚,要么晚饭后从启东绕道回海门。他亲自动手下厨,盐汁螃蜞、清蒸鲥鱼、洋扁豆炒咸瓜、土豆烧白菜等农家菜和高粱烧饼很快上了桌。晚餐时,老仇和父亲回味着当年围场上的点点滴滴,几杯崇明老米酒下肚后,越来越投缘。农家餐桌前,父亲曾经的风华正茂虽已不再,我却依然感受到他难以忘怀的农村人围垦时的那份坚韧。
晚上7点半,老仇夫妇挥动的双手消失在后视镜中,汽车在宽敞清新的陈海公路上向东行驶。当年部队转业前,我在海军崇明岛舰上工作了3个整年,今天带着双亲重游崇明,心中有无限的感慨。返家的路上,我仍然放慢车速,车内父母聊着崇明与海永的笑声和回忆不断。
门前靓车不算富,家有父母才是福。家离我越来越近。车过崇启跨海大桥时,两侧桥灯很亮,我发现副驾驶车位上的母亲洋溢着幸福的笑脸,她手中紧抓的那只红色塑料袋不见了。
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, 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
 苏公网安备32068402000011号 备案/许可证号: 苏ICP备2022036442号-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:32120210016
苏公网安备32068402000011号 备案/许可证号: 苏ICP备2022036442号-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:32120210016 
